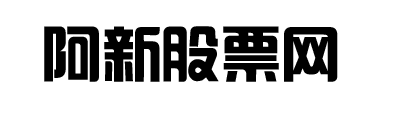南开区西南角永基花园的房子
我家以前就住永基对面bai我来告诉你吧
永基有du不好不好的传言~~都说那地下是坟墓以前那是zhi做生意的做什么什么赔从最初的永dao基商场就开始了
不是咱们迷信而是这些传言影响了永基的专地价
我个属人是不信这些的觉得无所谓并不是那的房子不好呵呵
房子质量来很差,连毛坯房都不算,里面都是干一半的工程垃圾。那次装东西,想借个电钻打眼儿,结果拿了个螺丝刀,敲了一下自,在墙上挖了个大洞。。用手指头一扣,里面都糟了。邻居家装修好多门口的墙都是空的,都是后来自己找砖头补的。而且基本每月停水好几次。有时候还特意周末停水,从早上起bai来就没水,下午四点多,才来水。大夏天晚上停水也是经常的。有时候水比咖啡色还深了。应急楼道伸手du不见五指,而且一点空气也没有。也没有灯。停电梯,走上去的话,能把人憋死在里面。因为影响了大娘zhi们乘凉,现在开始小区里连车都不让停了,大马路又修地铁。大家有钱还是考虑下周边的地方吧,这个小区应该炸了重盖。最有名的很多搬家公司都知道的一句话dao是:永基花园蟑螂真多!
,《财经》记者从天津市南开区政府办公室获悉,今年7月底,南开区政府已成立了由区长挂帅
,包括财政、公安、检察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专门处理天津永基集资案历史遗留问题,该工作组目标是确保
案件在今年内分步解决,并在明年北京奥运会前划上句号。
“我们年内的任务是,盘活已闲置多年的永基项目,同时结清所欠工程款和业主集资款。”南开区政府办
公室一位官员说。
轰动一时的天津永基集资案始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彼时,由港商梁志彬投资建设的天津永基花园,在
天津市、南开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兜售商铺、住房及台位、楼花等向京沪上万人募集资金14亿余元
。时至1998年,此举被定性为“乱集资”,港商悄然遁迹,房产证被废黜,多数业主血本无归。
九年来,永基案近万名业主自发组成业主委员会,遍访国务院法制办、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最高
人民法院以及天津各级部门,但法院一概不予立案,即使是中央部委出具的督办函件,亦成了地方执法部门相
互推搡的皮球。
今年6月3日,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7月5日,新华社报道称,因涉及严重违法违纪问题,中
央纪委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宋平顺党籍。
《财经》记者获悉,权威部门调查发现,宋平顺涉嫌利用职务为港商谋取利益,而宋袒护的对象之一,正
是已失踪多年的永基集资案主角梁志彬。
尘封多年的永基集资案由此被重新提及,业主们的举诉热情亦被再度激发,天津地方政府部门亦不得不采
取应对措施。
“市重点建设工程”
知情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商人梁志彬经人介绍与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宋平顺相识。梁
志彬的天津发展宏图,由此依托于宋氏资源一路开疆拓地。
1993年1月8日,天津永基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永基公司)成立,由梁志彬控制的香港基信企业有限公司
与隶属南开区建委的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合资组建。3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中,港方出资153万美元,占51%;中
方现金出资147万美元,占49%。
在合资公司中,梁志彬以控制人身份出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梁志彬拥有英国国籍,英文名为LEUNGCHI
PUN,其住址为香港跑马地山村道45-47号9楼。
永基公司成立仅四个月,宋平顺即跻身为天津市委常委,同时集天津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
局长于一身,权倾一时。
知情者称,正是经宋平顺帮助,永基公司顺利获得天津市政府批文,以批租形式取得位于天津市老城区和
内环线西侧的一块4万平方米土地的50年使用权,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的永基花园项目随之启动。
由于此项目头顶“旧城改造”光环,1994年9月15日,天津市政府下发“津政发[1994]4号”文件,将其列
为“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天津市、南开区两级政府的强势支持下,永基公司先后获得了房产开发的
“五证”。
在梁志彬的蓝图里,永基花园项目计划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工程建成商住楼两栋,住宅楼三栋及商城一
座,于1994年5月开工。
永基公司财务资料显示,截至1994年12月20日,项目已向京沪两地预售住宅、商铺共计人民币2亿元,实际
收入已达1.5亿元。依其预售程序,首批投资者与永基公司签定购房合同书,并由南开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
,时至1998年又获得了南开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双方同时约定,业主们委托永基物业公司代为
出租,并签定了租房协议书。
良好的预售记录,膨胀了梁志彬更大的财富野心。至1995年1月,经天津市、南开区两级政府批准,永基公
司获准成立北京办事处,将预售范围扩大至全国。自此,永基公司将招商广告遍布京津两地,“市重点建设项
目”亦反复出现在广告中。
区别于前期预售,此后永基公司的房产销售已变成以商铺台位、住宅楼花的方式,变相吸纳社会资金。即
购买永基商城一个台位是8万元,两年固定回报26.6%,三至四年固定回报27%,约定的年限到期全部退还本金
。而交易双方的凭据仅为一张永基公司出具的票据。
显然,这一模式已经脱离了房地产交易中的产权概念,在买者与卖者之间构建的是一种债权关系,其后果
无异于以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
实际上,针对永基公司变相集资的质疑在当时已不绝于耳。1995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国信息报》,即以
“天津永基花园:是售台位?还是变相集资?”为题,对该项目提出公开质疑。该报道引述销售人员的话称,
北京有1700人购买了台位号。
《财经》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永基项目的销售在1996年至1998年达到高潮,有来自全国约12400余名业主
与永基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其中,不乏天津、南开的政府机构及官员。但这些所集资金并未被梁志彬用于永
基二期工程。
“区分处理”与“一刀切”
1998年国庆节刚过,永基项目的业主忽然收到永基公司的通知:永基项目涉嫌“乱集资”被列为违法项目
,之前的购房协议全部作废。这意味着所有投资者都被列为非法集资的参与者,风险自担,后果自负。
据悉,造成1998年拐点的原因,除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更主要在于永基项目开发历时三年有余,
永基集资事件已进入兑付高峰,港商梁志彬的资金链由此断裂。
1999年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文,将永基公司的集资回购业务定性为“乱集资”,由政府帮助
永基公司进行整顿,日常普通业务仍由永基公司办理。南开区政府办公室一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梁志彬在
当时曾被天津警方控制,但后经天津高层干预获释,自此不知所踪。
留在梁志彬身后的永基巨额财务黑洞,实际转移至永基公司的另一股东——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身上,由
于该公司隶属南开区建委,这无疑加重了善后工作的官方色彩。
事实证明,作为接盘者的南开区政府,动用了一切行政手段筹集兑付资金,甚至向区属部门摊派指标。当
地一官员回忆,连区属的中小学教师亦受些影响,腾挪其工资填补财务黑洞。
《财经》调查获知,在永基项目1.2万余名业主中,有6000多名一次性投资达数十万元,拥有购买合同、公
证书及房屋产权证;其余近6000名投入3万至7万元,仅有一张永基公司出具票据为证。但在善后过程中,政府
采取“一刀切”,即所有投资者均列为非法集资的参与者。
鉴于业主的反复信访,中国银监会在2001年曾专门召集天津市政府、南开区政府及部分业主举行协调会。
会上,银监会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对乱集资定性的文件,没有包括永基项目合法的买卖合同,及已取得产权证
的合同,这个问题是天津市政府的操作问题,应由天津市政府解决。
2001年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就永基集资案向央行天津分行批复称,“在处理中应注意区分以合法形式掩
盖非法集资性质的行为,与真实合法的房产交易行为。”
但到同年10月,永基公司与天津市、南开区两级房管局仍然发布了注销“房屋产权证”的告示,其理由是
:合同被中国人民银行定性为乱集资,废除了业主的合同和《产权证》,没收房产。
法院概不受理
从1999年起,形成了业主起诉永基公司的一个高潮。
1999年5月,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马明坚将永基公司告至天津市南开区法院,后者做出“[1999]南民初字第
30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马明坚之诉讼请求,理由是“有关行政部门将此案定性为乱集资,所以不属于法院处
理的范围”。
同年7月,张文凤将永基公司及北京两家报社告上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现年71岁的张文凤,在1996年7月与
永基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房产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预付174522元,被告以租金名义每年按20%付张回报,即
每年34904元。三年期满既可获得本金,亦能获得房产证。在1997年和1998年度,张分别获得了两年的租金回报
。但1999年因永基公司此行为被定性为乱集资,对方拒付回报及拒办房产证。与马明坚遭遇相似,张文凤的诉
讼被法院驳回。
1999年8月20日,于松年、刘文彪等北京籍六名业主前住天津市高院举诉,得到法院的答复是,“我们按中
国人民银行对永基公司乱集资的定性,接上级指示,凡永基公司的案件一律不受理。”
时至2001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向天津市高院发出函件,要求对张文凤等15人所涉的永基房地产
公司纠纷案,“请认真接谈,依法处理”。但天津各级法院对永基纠纷案仍概不受理。
2001年国庆节后,受害业主60余人前往天津市政府大楼上访,后被当地警方关押达30余天。
2003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向银监会、天津市高院等部门发函,“请酌处”一些北京业主的信访,至今亦
石沉大海。
知情人士称,自1999年至2003年期间,宋平顺身兼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职务,其在永基案中
上下其手,为各界所诟病。
《财经》记者获知,由于永基案迟迟得不到解决,业主中有15人半身不遂;北京籍业主王二立曾投资永基
项目50万元,因家境日下已于2006年跳楼自杀。
2007年夏天,宋平顺自杀使得尘封多年的永基案重新被人关注。8月1日,来自北京的71岁退役军人林汉,
再次就永基案前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这是过去九年间他第十次至该法院举诉,但一如既往地被告之不予立
案。
时至今日,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永基项目,矗立在天津闹市一隅,但门庭冷落,戒备森严。
据南开区政府办公室一官员介绍,政府曾将物业管理移交给天津另一大型国企,但九年来一直闲置未用。
目前考虑到的盘活资产方式主要是外租或外售,但由于产权模糊且担心业主闹事,相关方案迟迟难产。
该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在宋平顺案公开通报后,南开区政府已牵头成立工作组,以确保今年作为永基
案排忧解难年,明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全部解决
什么东西现在可以轻易接触到或者买到,几十年后会变的很少
十年,听上去貌似是一个特别特别长抄的过程,可比过程更丰富bai的,应该是其中的故事。十年,十年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原本单纯的事情变du的复杂,可以让友情变淡,可以让爱情疏远。总之,十年的力zhi量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关于现实这个问题跟dao朋友讨论过无...
其实是当时记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
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
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出处?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的说法出自“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实施的情况。
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分产责抄任制要求家庭分田承包,很多人思想转变不过来,就流传出这么个说法,意思袭是好不容易消灭了私有制,做到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结果分产到户以后又成了私有制了。
扩展资料: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我国农村旧的经bai营管理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第一,就全国来说,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低,主要是手工劳动,因此不适合大规模的经营,而将经营的单位划小到家庭,同这种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相适应。
第二,原来那种大规模经营下的集体劳动(改革前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du生产经营单位,农民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很难准确统计,因而必然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以zhi家庭为经济单位可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第三,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生命体,劳动对象的这种特性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责任心dao,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有助于这种要求的实现。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其实是当时记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
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
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从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
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禹作敏自称是邓小平的“好学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禹作敏多次希望邓小平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
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
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
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 本文固定链接: http://www.jsfengsu.com/gpkh/3778.html
- 转载请注明: admin 于 【阿新股票视频网】 发表